张中信历史文化散文集《成都书》 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
来源:未知作者:四川文学网发布时间:2018-07-02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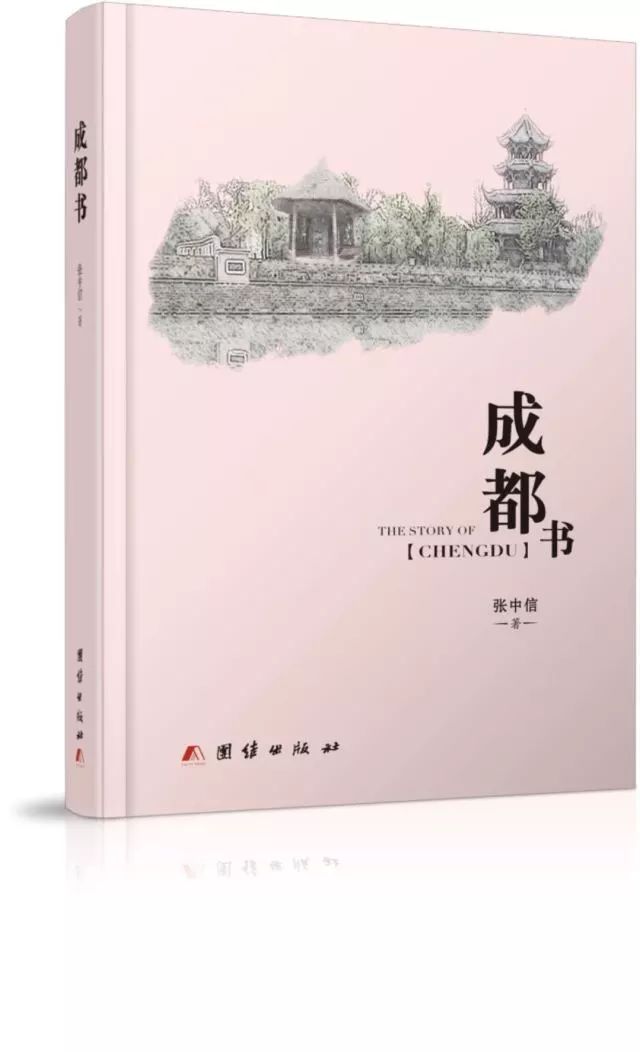
日前,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揭晓:张中信历史文化散文集《成都书》榜上有名。冰心散文奖是根据中国散文学会已故名誉会长、著名作家冰心先生遗愿,经中国作协批准,由中国散文学会于2000年设立实施的一项全国性散文评选,全国已先后有铁凝、张抗抗等多位当代著名作家和散文新秀获此殊荣。
《成都书》以三千年成都历史为线索,从影响成都的人物、事件等多角度重现成都人文历史,反映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从中折射出特有的成都气质和天府文化精神,再现李冰、司马相如、杨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陆游、苏东坡等历史人物“出蜀”、“入蜀”“读蜀”的人生历程。该书用文学的笔调再现历代历史人物对成都的影响,再现成都历史的文化积淀,对丰富巴蜀文明和发展天府文化的,为推进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成都书》以三千年成都历史为线索,从影响成都的人物、事件等多角度重现成都人文历史,反映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从中折射出特有的成都气质和天府文化精神,再现李冰、司马相如、杨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陆游、苏东坡等历史人物“出蜀”、“入蜀”“读蜀”的人生历程。该书用文学的笔调再现历代历史人物对成都的影响,再现成都历史的文化积淀,对丰富巴蜀文明和发展天府文化的,为推进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张中信是近年来活跃在巴蜀文坛的实力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成都市青羊区文联副主席。其散文创作别具一格,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乡土特色,擅长跨文体写作和诗意的表达,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已出版《风流板板桥》《失语的村庄》《哦,野茶灞那些事儿》《神韵巴中》《野茶灞时光》等诗歌、散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25部。曾荣获第七届四川文学奖、第三届四川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入选数十家文本或选集。
成都:历史的星空
——张中信历史文化散文集《成都书》六人谈

——张中信历史文化散文集《成都书》六人谈

石 英(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出版《石英散文集》《石英美文集》等散文、小说著作60余部)
张中信近年来致力于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推出了历史文化散文集《成都书——历代文人与成都》。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心灵史,张中信引领我们穿越千年曲径通幽的文化长廊,叩开历史之门,那些越走越远的文化巨人与我们的温暖地相遇了。
在本书的写作中,张中信的灵魂与先贤对接,在精神的一次次契合中,沛然出一种荡气回肠的人文情怀。这些历史文化人物虽然都是独立成篇,我们读完以后却总觉得有一团氤氲的气息笼罩着,有一个文脉场在呼吸跳跃。这个气息就是一种从家到国、由个体到群体、由片段到天下苍生的宏观精神场域。张中信的《成都书》主调是凭借影响成都的决定着历史文化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文化的历史走向和文人的人格构成。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一个地域的风骨与品质。当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投影在成都这片土地上,就形成了成都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认同。张中信苦苦探寻的文化现象,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精神向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观照到“文以化成”的朴素、温暖、敦厚的生命情怀。不妨这样说,张中信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中国文人的命运在成都平原的一个走向!是灿烂的星辰在生命个体的辉映!是历史的涛声拍打心岸的回响!
《成都书》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鸿,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忽而委婉,忽而热情地叙述着历史人物们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成都的风土人情、审美场景。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历史文化名人思想和情怀的展现。如在《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文中,作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写出了李白的文化性格,也写出了唐文化兴盛的风起云涌,成为他恰如其分地阐释构成成都文明底蕴的生动、形象的材料。其他如《细雨骑驴入剑门》中的陆游、《前不见古人》中的陈子昂,《万里桥边女校书》的女诗人薛涛,都注意运笔的轻重浓淡,抑扬张驰,笔下波光流溢。张中信始终在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这种语言不是他乡土题材的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是一种潮一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开始在一种哲理的词语中栖身。这应该是他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独特手法和别样风格。
《成都书》分为散文和诗歌两卷。在诗歌卷《成都书》中,作者以200多首新古体诗的形式,全方位吟咏成都的历史人物、山川风物、民情民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样的创作气势,这样的布局选材,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样的集中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也有点“前无古人”。
散文和新古体诗两卷《成都书》,既有理性叙述也有诗意审美,相互映照,熠熠生辉。从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以虔诚于历史的眼光对成都予以新颖的解读,立体的、全方位的向世人展现成都历史文化的神韵风采,更是对弘扬巴蜀文明和发展天府文化的美丽贡献。
在本书的写作中,张中信的灵魂与先贤对接,在精神的一次次契合中,沛然出一种荡气回肠的人文情怀。这些历史文化人物虽然都是独立成篇,我们读完以后却总觉得有一团氤氲的气息笼罩着,有一个文脉场在呼吸跳跃。这个气息就是一种从家到国、由个体到群体、由片段到天下苍生的宏观精神场域。张中信的《成都书》主调是凭借影响成都的决定着历史文化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文化的历史走向和文人的人格构成。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一个地域的风骨与品质。当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投影在成都这片土地上,就形成了成都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认同。张中信苦苦探寻的文化现象,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精神向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观照到“文以化成”的朴素、温暖、敦厚的生命情怀。不妨这样说,张中信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中国文人的命运在成都平原的一个走向!是灿烂的星辰在生命个体的辉映!是历史的涛声拍打心岸的回响!
《成都书》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鸿,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忽而委婉,忽而热情地叙述着历史人物们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成都的风土人情、审美场景。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历史文化名人思想和情怀的展现。如在《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文中,作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写出了李白的文化性格,也写出了唐文化兴盛的风起云涌,成为他恰如其分地阐释构成成都文明底蕴的生动、形象的材料。其他如《细雨骑驴入剑门》中的陆游、《前不见古人》中的陈子昂,《万里桥边女校书》的女诗人薛涛,都注意运笔的轻重浓淡,抑扬张驰,笔下波光流溢。张中信始终在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这种语言不是他乡土题材的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是一种潮一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开始在一种哲理的词语中栖身。这应该是他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独特手法和别样风格。
《成都书》分为散文和诗歌两卷。在诗歌卷《成都书》中,作者以200多首新古体诗的形式,全方位吟咏成都的历史人物、山川风物、民情民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样的创作气势,这样的布局选材,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样的集中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也有点“前无古人”。
散文和新古体诗两卷《成都书》,既有理性叙述也有诗意审美,相互映照,熠熠生辉。从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以虔诚于历史的眼光对成都予以新颖的解读,立体的、全方位的向世人展现成都历史文化的神韵风采,更是对弘扬巴蜀文明和发展天府文化的美丽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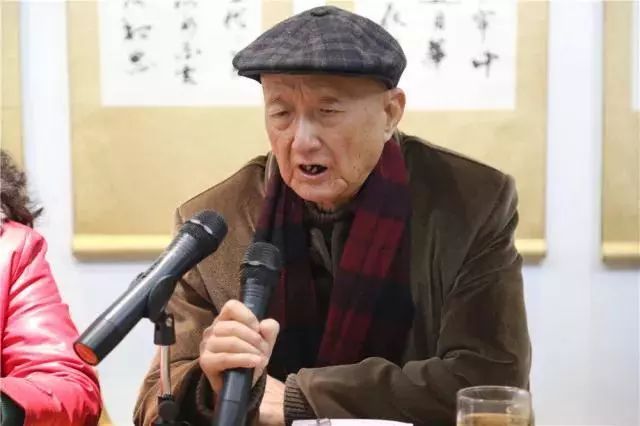
卢子贵(四川省散文学会会长。出版《走马吟》《步步走来》散文集12部,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
张中信其人,慷慨豪迈、潇洒磊落、极重义气,具有典型的大巴山人性情。加之他本人学识丰厚、文笔敏锐、勤奋著书,创作了丰富的具有人文情怀的著作。
在这本历史文化散文集中,作者选取了十一位与成都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司马相如、陈子昂、薛涛、花蕊夫人、杨慎、李调元、张问陶,每一个人都独立成篇,作者用独到的见解、优美的文笔,书写了这些历史人物在成都的生活经历、爱好追求、文学成就和人生命运。张中信这部历史文化散文集,从纯粹的文人作品中突围出来,直接对接中国当代文人的精神世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人生态度,让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回归到大地,回归到茅庵草舍,回归到喜怒哀乐的真实生活之中。
比如,作者在写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文中说:“想想梦中的玄妙,看看现实的残酷;官场的污浊,让诗人激灵中猛然坐起,仰天长啸,发出内心痛苦而悲愤的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华夏幸甚,有此李太白,文坛不寂寞;有此诗一首,沧桑不蹉跎。至此,李白的诗歌艺术水准跃上唐代文学的巅峰,而李白也说出了千百年来文人想说又不敢说那句话:摧眉折腰事权贵,自古文人不开心。作者这样评价李白,新意顿现,让人精神一振。让我们站在现实人生的场景,回望千年李白,深刻地认识到,李白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他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对封建社会践踏扭曲人性,所发出的控诉和悲愤呐喊。
张中信这部《成都书》之所以耐读,不仅仅在于他对历史人物的精彩描摹,更重要的是他借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心、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与绝妙见解。文以载道,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在当下的中国散文领域,能有这样的胸襟与见识的作家实在难得。张中信的散文创作题材广泛,成就斐然,在当今的四川文坛也属可圈可点,我被张中信如此历史辩证的哲思,如此开阔厚实的胸襟所折服。
张中信其人,慷慨豪迈、潇洒磊落、极重义气,具有典型的大巴山人性情。加之他本人学识丰厚、文笔敏锐、勤奋著书,创作了丰富的具有人文情怀的著作。
在这本历史文化散文集中,作者选取了十一位与成都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司马相如、陈子昂、薛涛、花蕊夫人、杨慎、李调元、张问陶,每一个人都独立成篇,作者用独到的见解、优美的文笔,书写了这些历史人物在成都的生活经历、爱好追求、文学成就和人生命运。张中信这部历史文化散文集,从纯粹的文人作品中突围出来,直接对接中国当代文人的精神世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人生态度,让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回归到大地,回归到茅庵草舍,回归到喜怒哀乐的真实生活之中。
比如,作者在写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文中说:“想想梦中的玄妙,看看现实的残酷;官场的污浊,让诗人激灵中猛然坐起,仰天长啸,发出内心痛苦而悲愤的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华夏幸甚,有此李太白,文坛不寂寞;有此诗一首,沧桑不蹉跎。至此,李白的诗歌艺术水准跃上唐代文学的巅峰,而李白也说出了千百年来文人想说又不敢说那句话:摧眉折腰事权贵,自古文人不开心。作者这样评价李白,新意顿现,让人精神一振。让我们站在现实人生的场景,回望千年李白,深刻地认识到,李白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他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对封建社会践踏扭曲人性,所发出的控诉和悲愤呐喊。
张中信这部《成都书》之所以耐读,不仅仅在于他对历史人物的精彩描摹,更重要的是他借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心、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与绝妙见解。文以载道,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在当下的中国散文领域,能有这样的胸襟与见识的作家实在难得。张中信的散文创作题材广泛,成就斐然,在当今的四川文坛也属可圈可点,我被张中信如此历史辩证的哲思,如此开阔厚实的胸襟所折服。

桥 歌(本名乔德春,现任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公开出版文学著作9部;其中多篇 荣获全省全国奖项。)
天府文化博大精深,如江似海;天府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群星,天府山川风物举世无双。巴蜀作家、诗人张中信酷爱文学,十年前从川东北的大巴山中,来到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徜徉在天府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如鱼得水,畅游尽欢。他在吸收天历史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潜心研习,不断深耕,让自己的灵魂在一次次的洗礼中火花四溅,美丽绽放;阅尽天府春色,采摘白花酿蜜,穷尽生命力道,铸造灵魂精华,最后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蜜汁变成一个个文化符号。张中信新古体诗集《成都书》,可谓诗人在天府文化领域中的生命礼赞和诗意结晶。
纵观张中信新古体诗集《成都书》,诗人紧紧追寻天府历史文化名人的踪迹,竭力搜寻其在岁月之河中的生命辉光,在那些感天动地的博大文化积淀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寄托,情感上的陶冶和思想上的升华,从而给读者绘制出了一幅幅或波涛壮阔,或感人肺腑,或风光旖旎,或故土相思的人文画卷。
《成都书》的主基调就是讴歌天府历史文化,赞颂天府自然美景。首篇组诗《天府文踪》,诗人以旅行者的身份,云游四方,遍访天府名山大川,最后聚焦在历史文化名人身上。通过梳理生长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名人的足迹,勾勒出巴蜀大地的山光物态,从而展示出天府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重要地位。在《锦城怀李白》中,诗人满怀敬仰之情,将“诗仙”李白的坎坷一生作了高度浓缩和概括。“长安忆逐臣,蜀地洗烦恼。”昔日的唐代都城长安,上层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天纵英才的李白本该得到重用,可是却落得被“逐”出京城的可悲下场。一个“逐”字,使我们看见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争斗的刀光剑影和官场的丑恶嘴脸。诗人只有在山水田园,在民风纯朴,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才能“洗”去心中的郁闷和烦恼。
作者对“诗圣”杜甫更是情有独钟,在《浣花忆杜甫》《杜甫草堂》和《游杜甫草堂》诗中,杜甫坎坷的一生和博大的精神世界跃然纸上。特别是“山河破碎时,黎庶涕泪出”和“蓟北传收日,狂喜谁似公?”两联,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杜甫那种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不是仅仅在缅怀和追思历史文化名人,而是通过这种追思,来反思和探究当前的社会现实,让人们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天府历史文化?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继往开来,使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大繁荣,大发展!
在赞颂天府自然美景的同时,诗人又将更多的色彩落笔在大成都这个区域內,将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今昔对照中,突显大成都的巨大变化,并且发出了“岁月谁守望?我似楚狂人”的主人翁豪情。组诗《锦西诗抄》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你看:青幽古老的青城山、鹤鸣山,携着中华道教的氤氲和袍服,穿越千年的历史篱笆,在“烟火关离魂”“拔雾见酒幡”中,食着人间烟火,以新颖的姿态,呈现在川西大地上,传播道教文化,祈祷众生万福,让华夏子孙万代“来去皆安心”!当年李冰父子带领巴蜀儿女降伏孽龙,治理岷江水患的情景如在眼前。诗人由衷感叹:“巴蜀润泽地,父子功盖天。”一心为老百姓着想,造福人民的英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张中信深谙中国古典诗歌的内核,在继承古典诗歌精华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新古体诗语言风格。细细品读张中信的新古体诗,音步和节奏都是非常和谐的,给人一种有条不紊,跌宕有致,抑扬错落的空间美感。可以说,他的诗歌语言本身的频率和张力已经赋予了音乐的神韵,形成动听的音乐氛围,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到诗的意境之中。读张中信的诗使我感到,现如今写诗的人不少,但好诗却不多。特别是一些现代人写的古体诗,要么生搬硬套,用一些深僻的字词假装门面;要么用一些花拳绣腿的伎俩,自以为是,不知所云。张中信的诗来自于民间,一直生活在民间。他一直在找寻生活的呼吸,一直在给诗歌寻找一个氧吧之类的平台,让自己的诗歌通过口语活着。特别是他的一系列描写川西坝子农村的山水田园诗,不仅接地气,而且充溢着泥土味。我想,称张中信 为当代“新山水田园诗”创作的领头雁,似乎一点也不过份!
阅读张中信《成都书》这些触及心灵的新古体诗,不仅使阅读者能够立体的、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天府历史文化的神韵风采,而且可以抵达一个诗人诗性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去感受和倾听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闪电,以及发自肺腑的浅吟低唱的生命放歌!
天府文化博大精深,如江似海;天府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群星,天府山川风物举世无双。巴蜀作家、诗人张中信酷爱文学,十年前从川东北的大巴山中,来到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徜徉在天府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如鱼得水,畅游尽欢。他在吸收天历史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潜心研习,不断深耕,让自己的灵魂在一次次的洗礼中火花四溅,美丽绽放;阅尽天府春色,采摘白花酿蜜,穷尽生命力道,铸造灵魂精华,最后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蜜汁变成一个个文化符号。张中信新古体诗集《成都书》,可谓诗人在天府文化领域中的生命礼赞和诗意结晶。
纵观张中信新古体诗集《成都书》,诗人紧紧追寻天府历史文化名人的踪迹,竭力搜寻其在岁月之河中的生命辉光,在那些感天动地的博大文化积淀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寄托,情感上的陶冶和思想上的升华,从而给读者绘制出了一幅幅或波涛壮阔,或感人肺腑,或风光旖旎,或故土相思的人文画卷。
《成都书》的主基调就是讴歌天府历史文化,赞颂天府自然美景。首篇组诗《天府文踪》,诗人以旅行者的身份,云游四方,遍访天府名山大川,最后聚焦在历史文化名人身上。通过梳理生长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名人的足迹,勾勒出巴蜀大地的山光物态,从而展示出天府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重要地位。在《锦城怀李白》中,诗人满怀敬仰之情,将“诗仙”李白的坎坷一生作了高度浓缩和概括。“长安忆逐臣,蜀地洗烦恼。”昔日的唐代都城长安,上层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天纵英才的李白本该得到重用,可是却落得被“逐”出京城的可悲下场。一个“逐”字,使我们看见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争斗的刀光剑影和官场的丑恶嘴脸。诗人只有在山水田园,在民风纯朴,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才能“洗”去心中的郁闷和烦恼。
作者对“诗圣”杜甫更是情有独钟,在《浣花忆杜甫》《杜甫草堂》和《游杜甫草堂》诗中,杜甫坎坷的一生和博大的精神世界跃然纸上。特别是“山河破碎时,黎庶涕泪出”和“蓟北传收日,狂喜谁似公?”两联,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杜甫那种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不是仅仅在缅怀和追思历史文化名人,而是通过这种追思,来反思和探究当前的社会现实,让人们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天府历史文化?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继往开来,使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大繁荣,大发展!
在赞颂天府自然美景的同时,诗人又将更多的色彩落笔在大成都这个区域內,将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今昔对照中,突显大成都的巨大变化,并且发出了“岁月谁守望?我似楚狂人”的主人翁豪情。组诗《锦西诗抄》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你看:青幽古老的青城山、鹤鸣山,携着中华道教的氤氲和袍服,穿越千年的历史篱笆,在“烟火关离魂”“拔雾见酒幡”中,食着人间烟火,以新颖的姿态,呈现在川西大地上,传播道教文化,祈祷众生万福,让华夏子孙万代“来去皆安心”!当年李冰父子带领巴蜀儿女降伏孽龙,治理岷江水患的情景如在眼前。诗人由衷感叹:“巴蜀润泽地,父子功盖天。”一心为老百姓着想,造福人民的英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张中信深谙中国古典诗歌的内核,在继承古典诗歌精华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新古体诗语言风格。细细品读张中信的新古体诗,音步和节奏都是非常和谐的,给人一种有条不紊,跌宕有致,抑扬错落的空间美感。可以说,他的诗歌语言本身的频率和张力已经赋予了音乐的神韵,形成动听的音乐氛围,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到诗的意境之中。读张中信的诗使我感到,现如今写诗的人不少,但好诗却不多。特别是一些现代人写的古体诗,要么生搬硬套,用一些深僻的字词假装门面;要么用一些花拳绣腿的伎俩,自以为是,不知所云。张中信的诗来自于民间,一直生活在民间。他一直在找寻生活的呼吸,一直在给诗歌寻找一个氧吧之类的平台,让自己的诗歌通过口语活着。特别是他的一系列描写川西坝子农村的山水田园诗,不仅接地气,而且充溢着泥土味。我想,称张中信 为当代“新山水田园诗”创作的领头雁,似乎一点也不过份!
阅读张中信《成都书》这些触及心灵的新古体诗,不仅使阅读者能够立体的、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天府历史文化的神韵风采,而且可以抵达一个诗人诗性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去感受和倾听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闪电,以及发自肺腑的浅吟低唱的生命放歌!

袁瑞珍(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作品获四川省散文学会十佳散文奖、第二届四川散文奖。)
不久前与张中信先生相识,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豪放性情中透着一股儒雅之气,而他的文字也如其人般呈现出清丽飘逸或凝重老道;犀利明快或幽默调侃等多面性特征。
十年前,张中信辞别故土,辞别官场,来到成都这座被三千多年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做了个“休闲文人”。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革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他的情绪不由得激动澎湃起来,他的思想、视野和胸怀变得深邃开阔起来,他开始了一项艰难而充满挑战性的工作,研究蜀地文明,仰望成都的历史文化天空,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梳理三千年的历史文脉。于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和姊妹篇新古体诗集《成都书》诞生了!我抛开一切物事,沉下心来,用两天的时间细细地阅读,沉浸于中。
当张中信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与作家,带着他的思考,用他独特的文字和叙事风格,梳理着成都这座不朽的城市三千年的文脉,向我们展示出蜀地耀眼的历史文化巨星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时,我的心也浸润在蜀地这片沃土上,我的眼睛也凝望着蜀地这片耀眼的天空,穿越三千年的时间隧道,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司马相如、陈子昂、薛涛、花蕊夫人、杨慎、李调元、张问陶温柔相遇了,他们让我心潮澎湃,也让我潸然泪下。
《成都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清雅诗意、愤激昂扬、轻盈调侃的文字。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去书写闪耀蜀地、闪耀中华的这11位历史文化巨人。刚翻开书页,那描写李白出生地的“漫坡渡”,就把我带入神仙般的境地:“水是那样清,远远看去,云蒸雾腾,有些淡淡的白雾。天和水是不大分得清的,真是漫坡!岸上是一遍淡黄的花树,夹着一些青竹,有些飘渺,有些空灵。”这样的文字,立刻让人联想到“诗仙”李白就应该出生在这样的仙境之中。对一代“诗圣”杜甫,文字则慷慨激越起来。当杜甫迈着沉滞的脚步,脸上布满忧国忧民的幽思和痛苦,行走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泥泞起伏的小径上,面对“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朝廷政局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居住的草堂因秋风暴雨的摧残而飘摇坍塌,联想到自己几十年来颠沛流离的所见所闻,再也无法忍受压抑在心中的无限悲愤,写下了锥心泣血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悲天悯人的绝世呼喊,令张中信热血喷张,他写道:“这呐喊声,穿越千年时空,在天府成都久久回荡,在华夏大地浩浩飘扬……”这样的文字,怎能不在我的心里激起千层波浪万顷海涛?
对被称为《赋圣》的司马相如和陈子昂,张中信的文字则显得轻快起来,他用略带调侃意味的文字,书写了司马相如财色兼收,是为御用文人歌功颂德的竞相夸耀和身处官场的无奈,还写了陈子昂因家境富阔,在年少时的顽皮和骄奢,为出名不惜将用高价拍到的古琴抡斧劈之的场面。这种在同一本书中,根据不同人物所处的不同政治环境、时代特征和人生际遇,使用不同的文字风格书写不同人物形象的文章,的确不能不让我对张中信驾驭文字的功夫而感叹而赞赏!
脱俗的见解,赋予了这本书独特的气质。《成都书》不仅还原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真实的社会背景、生活境遇、成长历程,刻画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浸润、中国文人关注人民苦难、为国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在书写李白、杜甫等11个名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中,理性地审视和整理出中国历史文脉的走向,对一些历史文化名人不同的命运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及一些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脱俗的见解。如他剖析了李白不能施展政治抱负的原因后提出:“如果玄宗皇帝不把李白送出长安,李白最终也成不了政治家,而中国诗坛上就不可能有一颗最闪亮的诗星,也就出不了这位‘诗仙’了”。对杜甫的忧国忧民,揭示人间苦难的诗作,最终演绎为中国诗坛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但为什么却一生饱受苦难的原因,提出是因为“冷僻、生硬、苦涩、充满苦难感和火药味,读来让人压抑,让那些粉饰太平的官吏反感”,也不考虑统治者皇帝的感受,就那么真实地反映战乱带给国家、带给人民,带给自己的苦难。所以他受到人民的喜爱却不受统治者的待见。在《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文中,针对杨贵妃“红颜误国”的说法为杨贵妃正名,他说:“后人老爱评说杨玉环红颜误国,殊不知那位老玄宗治国理政三十多年,早已激情消磨,更兼迷恋长生不老,荒废朝政久矣,大唐帝国的式微已是必然,与杨玉环又有多大关系呢?试想,一个红颜女子都可以祸乱的国家,它的政权还有延续的价值吗?”这些见解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的确发人深省!
张中信从三千年的历史中,梳理出这11个人对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体系的贡献,诠释着蜀地这块温润丰腴的土地对他们的滋养和包容,他们闪耀的诗魂和精神也沉淀在成都平原敦厚绵长而灵动的历史中,深刻地影响着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灵魂和风骨。因此梳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对成都这座城市的影响,就寻找到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明走向,为我们弘扬蜀地文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让这座古老的城市诗意地、充满活力地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让灿烂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想这大概就是张中信写作《成都书》的初衷吧!
不久前与张中信先生相识,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豪放性情中透着一股儒雅之气,而他的文字也如其人般呈现出清丽飘逸或凝重老道;犀利明快或幽默调侃等多面性特征。
十年前,张中信辞别故土,辞别官场,来到成都这座被三千多年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做了个“休闲文人”。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革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他的情绪不由得激动澎湃起来,他的思想、视野和胸怀变得深邃开阔起来,他开始了一项艰难而充满挑战性的工作,研究蜀地文明,仰望成都的历史文化天空,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梳理三千年的历史文脉。于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和姊妹篇新古体诗集《成都书》诞生了!我抛开一切物事,沉下心来,用两天的时间细细地阅读,沉浸于中。
当张中信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与作家,带着他的思考,用他独特的文字和叙事风格,梳理着成都这座不朽的城市三千年的文脉,向我们展示出蜀地耀眼的历史文化巨星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时,我的心也浸润在蜀地这片沃土上,我的眼睛也凝望着蜀地这片耀眼的天空,穿越三千年的时间隧道,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司马相如、陈子昂、薛涛、花蕊夫人、杨慎、李调元、张问陶温柔相遇了,他们让我心潮澎湃,也让我潸然泪下。
《成都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清雅诗意、愤激昂扬、轻盈调侃的文字。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去书写闪耀蜀地、闪耀中华的这11位历史文化巨人。刚翻开书页,那描写李白出生地的“漫坡渡”,就把我带入神仙般的境地:“水是那样清,远远看去,云蒸雾腾,有些淡淡的白雾。天和水是不大分得清的,真是漫坡!岸上是一遍淡黄的花树,夹着一些青竹,有些飘渺,有些空灵。”这样的文字,立刻让人联想到“诗仙”李白就应该出生在这样的仙境之中。对一代“诗圣”杜甫,文字则慷慨激越起来。当杜甫迈着沉滞的脚步,脸上布满忧国忧民的幽思和痛苦,行走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泥泞起伏的小径上,面对“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朝廷政局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居住的草堂因秋风暴雨的摧残而飘摇坍塌,联想到自己几十年来颠沛流离的所见所闻,再也无法忍受压抑在心中的无限悲愤,写下了锥心泣血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悲天悯人的绝世呼喊,令张中信热血喷张,他写道:“这呐喊声,穿越千年时空,在天府成都久久回荡,在华夏大地浩浩飘扬……”这样的文字,怎能不在我的心里激起千层波浪万顷海涛?
对被称为《赋圣》的司马相如和陈子昂,张中信的文字则显得轻快起来,他用略带调侃意味的文字,书写了司马相如财色兼收,是为御用文人歌功颂德的竞相夸耀和身处官场的无奈,还写了陈子昂因家境富阔,在年少时的顽皮和骄奢,为出名不惜将用高价拍到的古琴抡斧劈之的场面。这种在同一本书中,根据不同人物所处的不同政治环境、时代特征和人生际遇,使用不同的文字风格书写不同人物形象的文章,的确不能不让我对张中信驾驭文字的功夫而感叹而赞赏!
脱俗的见解,赋予了这本书独特的气质。《成都书》不仅还原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真实的社会背景、生活境遇、成长历程,刻画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浸润、中国文人关注人民苦难、为国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在书写李白、杜甫等11个名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中,理性地审视和整理出中国历史文脉的走向,对一些历史文化名人不同的命运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及一些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脱俗的见解。如他剖析了李白不能施展政治抱负的原因后提出:“如果玄宗皇帝不把李白送出长安,李白最终也成不了政治家,而中国诗坛上就不可能有一颗最闪亮的诗星,也就出不了这位‘诗仙’了”。对杜甫的忧国忧民,揭示人间苦难的诗作,最终演绎为中国诗坛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但为什么却一生饱受苦难的原因,提出是因为“冷僻、生硬、苦涩、充满苦难感和火药味,读来让人压抑,让那些粉饰太平的官吏反感”,也不考虑统治者皇帝的感受,就那么真实地反映战乱带给国家、带给人民,带给自己的苦难。所以他受到人民的喜爱却不受统治者的待见。在《长安不见使人愁》一文中,针对杨贵妃“红颜误国”的说法为杨贵妃正名,他说:“后人老爱评说杨玉环红颜误国,殊不知那位老玄宗治国理政三十多年,早已激情消磨,更兼迷恋长生不老,荒废朝政久矣,大唐帝国的式微已是必然,与杨玉环又有多大关系呢?试想,一个红颜女子都可以祸乱的国家,它的政权还有延续的价值吗?”这些见解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的确发人深省!
张中信从三千年的历史中,梳理出这11个人对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体系的贡献,诠释着蜀地这块温润丰腴的土地对他们的滋养和包容,他们闪耀的诗魂和精神也沉淀在成都平原敦厚绵长而灵动的历史中,深刻地影响着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灵魂和风骨。因此梳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对成都这座城市的影响,就寻找到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明走向,为我们弘扬蜀地文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让这座古老的城市诗意地、充满活力地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让灿烂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想这大概就是张中信写作《成都书》的初衷吧!

万郁文 (出版散文集《追梦》,主编《少城文史》。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我得到《成都书》这本书就爱不释手,挑灯夜读,仿佛穿越时空,和书中的蜀中文豪、俊郎才女相拥吟唱,度过了千年时光,抚摸着他们一生的轨迹和诗篇,将我的头脑装满这些升跃在星空的文坛上的一颗颗明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让我与之执手,内心充满感激和激越的情素。
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这是一本书写历代文人与成都的书。书中书写了在诗坛上、文学上光芒万丈的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司马相如、陈子昂、薛涛、花蕊、杨慎、李调元、张问陶十一位文化巨星,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和他们的惊世流传的诗作。让我们轻松地和他们握了一次手。张中信早已著作等身,这本《成都书》他跳开了他熟悉的家乡的那些人和那些事的题材,选择了与成都有关联的十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来写作,这样难度更大,花费的精力更多,我认为这本书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突破。
原本我以为张中信是学文科出生,哪知他是经济学研究生,但是他对历史的研究,古典诗词的理解,文章的写作结构,是一个学文学的研究生难于达到的水平。书中每一篇文章,作者是以书写人物的诗为主轴,将诗歌巧妙的用于文中,也以诗歌反映人物的思想境界、精神领域和生平时态,每写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段生平,都有诗歌来佐证,增加了对事件真实性、可靠性的认可。因为千年历史,后人全凭史料记载来考证,有了这些诗词的印证,可以毫不怀疑当时发生的事情。
最让人读来有收益的是,以前学习,背诵的好多古诗,找到了出处。比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老少都知晓的诗,是在李白出川漫游,离开巴山蜀水好些年,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客栈,看到天上的月亮,忽然思念起天府巴蜀的亲人来,他含泪吟唱出了这首思乡名篇《静夜思》。
杜甫一生也是坎坷,经历了“三吏”“三别”,后来转站来到成都,在“万里桥西宅门,百花潭北庄”的草堂住下。成都平原潮湿的气候和夏季的暴雨,将杜甫的茅舍吹到,他们全家老少顷刻无家可归,露宿在风雨中,由此他想到和他一样居住在茅屋中被暴风雨吹垮房屋的百姓,要是有能够有抵挡风雨的大房子该多好啊。于是,杜甫锥心滴血的写下了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文豪苏轼也是给后人留下很多诗篇,最有名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词,是站在黄州城西临长江中有一座巨大石崖上,面对滔滔长江,回想起这条江上曾经发生过的血与火的战争,禁不住豪情万丈,写下了《念奴娇 赤壁怀古》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的。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写的非常鲜活,仿佛就是作者的朋友一样,让我们感到不是在读史料,而是作者身边的人,是作者非常熟悉的人,读起来很亲切、很感人。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小标题都是用所写人物的诗句作的,更加增添了本书的文学色彩。另一大特色是每一篇文章,就是每个人物的最后一节,作者给予了一定的评论,让你能够把握住这个人物的形象。不是简单的抒写完了事,而是有一定的见解和历史定位,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但对这本书中所写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增添了对这些蜀中文豪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认知和思考。
我得到《成都书》这本书就爱不释手,挑灯夜读,仿佛穿越时空,和书中的蜀中文豪、俊郎才女相拥吟唱,度过了千年时光,抚摸着他们一生的轨迹和诗篇,将我的头脑装满这些升跃在星空的文坛上的一颗颗明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让我与之执手,内心充满感激和激越的情素。
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这是一本书写历代文人与成都的书。书中书写了在诗坛上、文学上光芒万丈的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司马相如、陈子昂、薛涛、花蕊、杨慎、李调元、张问陶十一位文化巨星,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和他们的惊世流传的诗作。让我们轻松地和他们握了一次手。张中信早已著作等身,这本《成都书》他跳开了他熟悉的家乡的那些人和那些事的题材,选择了与成都有关联的十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来写作,这样难度更大,花费的精力更多,我认为这本书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突破。
原本我以为张中信是学文科出生,哪知他是经济学研究生,但是他对历史的研究,古典诗词的理解,文章的写作结构,是一个学文学的研究生难于达到的水平。书中每一篇文章,作者是以书写人物的诗为主轴,将诗歌巧妙的用于文中,也以诗歌反映人物的思想境界、精神领域和生平时态,每写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段生平,都有诗歌来佐证,增加了对事件真实性、可靠性的认可。因为千年历史,后人全凭史料记载来考证,有了这些诗词的印证,可以毫不怀疑当时发生的事情。
最让人读来有收益的是,以前学习,背诵的好多古诗,找到了出处。比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老少都知晓的诗,是在李白出川漫游,离开巴山蜀水好些年,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客栈,看到天上的月亮,忽然思念起天府巴蜀的亲人来,他含泪吟唱出了这首思乡名篇《静夜思》。
杜甫一生也是坎坷,经历了“三吏”“三别”,后来转站来到成都,在“万里桥西宅门,百花潭北庄”的草堂住下。成都平原潮湿的气候和夏季的暴雨,将杜甫的茅舍吹到,他们全家老少顷刻无家可归,露宿在风雨中,由此他想到和他一样居住在茅屋中被暴风雨吹垮房屋的百姓,要是有能够有抵挡风雨的大房子该多好啊。于是,杜甫锥心滴血的写下了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文豪苏轼也是给后人留下很多诗篇,最有名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词,是站在黄州城西临长江中有一座巨大石崖上,面对滔滔长江,回想起这条江上曾经发生过的血与火的战争,禁不住豪情万丈,写下了《念奴娇 赤壁怀古》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的。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写的非常鲜活,仿佛就是作者的朋友一样,让我们感到不是在读史料,而是作者身边的人,是作者非常熟悉的人,读起来很亲切、很感人。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小标题都是用所写人物的诗句作的,更加增添了本书的文学色彩。另一大特色是每一篇文章,就是每个人物的最后一节,作者给予了一定的评论,让你能够把握住这个人物的形象。不是简单的抒写完了事,而是有一定的见解和历史定位,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但对这本书中所写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增添了对这些蜀中文豪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认知和思考。

赖 静(青羊区作协副秘书长,四川文学网副主编,青年诗人,作家)
张中信其人,慷慨豪迈、潇洒磊落、极重义气,具有典型的秦巴汉子性情。他本人学识丰厚、文笔敏锐、勤奋著书,是位才情丰沛的作者。此番面世的《成都书》分为两册:新古体诗卷和散文卷,分别从诗歌和散文的体裁描写蜀地的风物人情、历史名人。
《成都诗》是张中信沿循古诗人的足迹,状写锦绣河山、记录平凡生活、讴歌天府文化、展现天府风貌的综合性人文画卷。
在《浣花溪忆杜甫》中,作者寥寥数字“锦西”“桃花艳”“豆角稀”,便勾勒出浣花溪的清丽景致。“万里悲秋恨,天地一首诗”更将杜甫当年寓居成都时的忧愁心境完美地融入其中。让人想起浣花溪时,不自觉思绪便飞回那段动荡不安的中唐岁月,同时也为命途坎坷的杜甫能在浣花溪拥有短暂安宁的生活而感到欣慰。
在《巴蜀风》中,张中信游历了蜀中的名山大川、老城古镇,用清婉秀丽的笔触以浪漫情怀描画了一副蜀中胜景图,多方位展示了巴蜀地区的迤逦风光和多彩民俗。《剑门关》的写法用典不绝、数字入诗堪称妙笔,比如“雄关”“飞鸟”取自李白《蜀道难》,“放翁开颜”来自陆游仕蜀。另外,“纵横离乱烟”一句颇具浪漫气息,将一幅漫漫雄关道的危崖风光展现得精绝壮丽。
尤为可贵的是,《浪子吟》向读者坦诚地展示了诗人人生中的痛苦、矛盾、不羁和不甘。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化作诗歌,同时充满了对挫折的不屑与抵抗。《感事》有言:
张中信其人,慷慨豪迈、潇洒磊落、极重义气,具有典型的秦巴汉子性情。他本人学识丰厚、文笔敏锐、勤奋著书,是位才情丰沛的作者。此番面世的《成都书》分为两册:新古体诗卷和散文卷,分别从诗歌和散文的体裁描写蜀地的风物人情、历史名人。
《成都诗》是张中信沿循古诗人的足迹,状写锦绣河山、记录平凡生活、讴歌天府文化、展现天府风貌的综合性人文画卷。
在《浣花溪忆杜甫》中,作者寥寥数字“锦西”“桃花艳”“豆角稀”,便勾勒出浣花溪的清丽景致。“万里悲秋恨,天地一首诗”更将杜甫当年寓居成都时的忧愁心境完美地融入其中。让人想起浣花溪时,不自觉思绪便飞回那段动荡不安的中唐岁月,同时也为命途坎坷的杜甫能在浣花溪拥有短暂安宁的生活而感到欣慰。
在《巴蜀风》中,张中信游历了蜀中的名山大川、老城古镇,用清婉秀丽的笔触以浪漫情怀描画了一副蜀中胜景图,多方位展示了巴蜀地区的迤逦风光和多彩民俗。《剑门关》的写法用典不绝、数字入诗堪称妙笔,比如“雄关”“飞鸟”取自李白《蜀道难》,“放翁开颜”来自陆游仕蜀。另外,“纵横离乱烟”一句颇具浪漫气息,将一幅漫漫雄关道的危崖风光展现得精绝壮丽。
尤为可贵的是,《浪子吟》向读者坦诚地展示了诗人人生中的痛苦、矛盾、不羁和不甘。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化作诗歌,同时充满了对挫折的不屑与抵抗。《感事》有言:
苦涩人生艰,历练几经年。
逆流横空出,坦途狂热喧。
心与冰雪近,耻向权贵言。
诗文休自菲,权作夕晖篇。
逆流横空出,坦途狂热喧。
心与冰雪近,耻向权贵言。
诗文休自菲,权作夕晖篇。
自古文人难于仕途,张中信也不例外。以他过往在地方工作的政绩和办企业的经济管理成就,他在蓉城本可大展身手。然而官场险恶、人心叵测,在大巴山的雄浑雨雾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张中信,为人豪气粗犷,这就注定他不是一个能在官场虚与委蛇的人。于是,我们才从这字字苦涩之中,体会到了他内心的不甘。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讲,如果不识其人只会看到他风流倜傥的一面,但如果对他深入了解,则会发现,他的身上充满了狂放与细腻、忧思与豁达、浪漫与现实,等理应矛盾的性格。但现实的奇妙在于,矛盾在他身上却得到了有机统一。
古体诗最难之处在于使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而张中信却能用朴实稳重的笔风勾勒出巴蜀的山川江河,用平实的语言凝练出成都的人情风貌。读张中信的古体诗,像是跟着他走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目睹了市民的安逸生活,也游遍了巴蜀的山川河流,并一窥川人奋发拼搏的精神。这精神贯通千年,从前人的诗句中得以窥见,也正在今天的川人身上迸发新的生命力!他的诗极少抒情,大多时候,他的诗宛若一个冷静坚韧的汉子,诚恳地叙写着天府之国的辉煌人文,不慌不忙地诉说自己的心得。在他的诗中,你还可以体会到他偶有迷茫,亦能守护初心的坚持与执着。
如果说张中信的古体诗适于晨读,那么他的人物散文就合于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是在深夜,一边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一边品读张中信的《成都书——历史文化散文集》。到后来,食不知味,佐酒的已非卤肉,而是那飞扬的文采、俊逸的才思和久远的故事。
这本散文集以大开大阖的笔法,汪洋恣肆地铺展开那些影响成都又被成都所影响的历史人物。你会在阅读李白的故事中,酣畅淋漓,忍不住浮一大白;也会在感伤杜甫的一生中,润湿眼角,酒难下咽;还会在怀想薛涛的生命中,情为之系,心头悄动。
我曾读过一本写隐士的书,大概由于部分人物的资料散佚,于是作者在写到人物生活的转折处时,也是语焉不详,让读者难以理解人物的行为和心境。诚然,隔着千年的历史云烟,我们难以看清当时人物的选择。但张中信以细腻的情思,真切地去揣摩人物的心理,所以呈现在作品中,每个人物的人生轨迹都是条理清晰、每段人物的心境行为都是合乎情理、每段人物的故事经历都是完整无缺。令人读来,没有丝毫遗憾。
人物传记不好写,难在于文风笔法的统一与变化。写作的人当然有其固定的文字风格,但笔下的人物却又各有各的性格。同一种笔调,描摹千人,那必然令人掩卷之后分不清谁是谁。但张中信于此,却颇有造诣。
书李白的浪漫、狂放和不羁,张中信的行文节奏便如临章草,洋洋洒洒,浑厚中带有奇趣。浑厚的是,他着重刻画人物的生活轨迹,尤其是李白游侠般的踪迹,让人神思远扬,忍不住想要追寻谪仙足迹浪荡江湖。书者必是有轻有重,这便是奇趣。奇在于哪儿?《将进酒》是流传至今不多的劝酒歌。作者在此,将李白的诗文与他和岑夫子丹丘生共饮谈话的情景,巧妙地融为一体,读来逸兴遄飞、一气呵成。作者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李白的浪漫与仙气。
述杜甫的坎坷、忧思与坚韧,张中信的行文风格便如拓魏碑,字字铿锵,古拙质朴中含着悲苦。古拙质朴是杜甫一生奔波迁徙、衣食难足的多舛命运;悲苦,不仅仅是杜甫忧天下之忧的悒郁,还有作者对杜甫艰辛命运的仰天叩问。写李白的汪洋笔意,到此,忽然收敛。你能真切地体会到文字中的阴郁气氛,感悟到行文外的不尽之意。
写苏轼的刚毅、不屈和痴情,张中信的行文笔调便如摹楷书,笔锋生动,刚劲峻拔而有情致。峻拔的是,他抒写东坡一生跌宕起伏的命运时一咏三叹。有情的是,作者不减笔墨地刻画了四位对苏轼一生影响深远的女性:苏母、王弗、王闰之、高太后。千古男权社会,作者非是一味展现东坡才情的个体自发性,而是带着客观、中肯的评价,肯定这四位女性对东坡诗文著作、乃至人生命运的积极影响。
当然还有更多精彩篇章需要读者自己去文中寻味。但这部《成都书》绝对能为更多的读者和不了解成都的人带去丰富的信息量。从《成都书》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张中信对成都的热爱,否则他不会辛勤著述如此斑斓的篇章。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76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768号